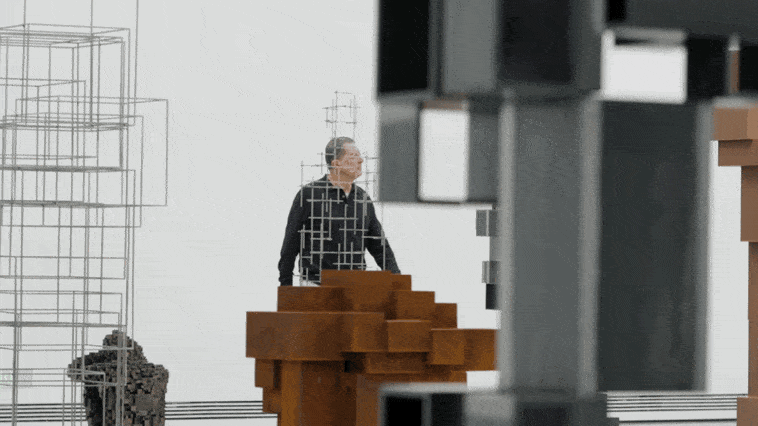Interview with Anthony Gormley 青岛个展:亚洲最全面、体量最大的创作呈现
英国雕塑家安东尼·葛姆雷(Antony Gormley),是当今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家之一。他持续创作人体雕塑、公共空间中的艺术近40年,获得包括透纳奖在内的众多奖项,作品遍布全球各大美术馆与艺术机构,还被英国前女王授予爵士称号。
时隔五年,今年四月底,葛姆雷再次来到中国,并带来了他在青岛西海美术馆的大型展览“有生之时”(Living Time)。这是迄今为止艺术家在亚洲最为全面、体量最大的创作呈现,39件雕塑,跨越他40多年的艺术职业生涯。
对于整个展厅最后呈现的效果,葛姆雷赞不绝口。他在布展时一直强调,不要开美术馆的射灯,只用自然光线。那种柔和而微妙的阳光,随着一天中时间而变化的光影,也成了展览的一部分。
但他还是这么做了——“也许我不够了解中国,但我觉得,中国人存在着巨大的焦虑,而展览的作品布置,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代人的现状。”
他开玩笑说,如果有观众看完了整个展览,却没有找到一件能够与之共鸣的作品,“那首先,整个展览是失败的,还有,我真的挺为他担心的。”
艺术家想用雕塑来表现那种没有边缘、无限延伸的空间感。“我们都是单独、不同的个体。有不同的品味,以不同的方式走路、说话和写作。但我们都能体验到那个普遍存在的空间。”
在展厅中,一件葛姆雷标志性的像素化作品,由数以千计、大小不同的钢块组成,12×25、25×25、50×50、100×100、200×200英尺等等。尽管形象高度模糊,我们还是能看出雕塑抱着头,有些绝望的落寞。
“作品《聚集I》是我第一次意识到,我可以用元素,从部分到整体去构筑空间。你可以看到这些钢块它们是相当粗糙的,还有焊接的烟熏在上面。”
“这两个悬浮着的《果实》和《身体》,它们把重力戏剧化了,《大地》和《最终产品》让这种漂浮感接了地。”葛姆雷说。
5号展厅中的这四件作品,有两件被钢缆吊起,两件被放在地上。
“果实或种子也是一种炸弹,这种潜力可以爆炸、表达和增殖。” 葛姆雷说。而这种增殖的观念也与作品的灵感来源息息相关——胎儿在母体中蜷缩的姿态。
“我觉得我在很多地方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启发,并且也将如此进行下去。”葛姆雷说。
“我马上会去韩国,因为我有两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永久性项目正在进行中。它们都至少要三年,甚至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,相当地复杂。”